阅读:0
听报道
撰文 | 赵晗 编辑 | 秦旭东

如果一位“北京阿姨”在京有三四套房子,有退休金,孩子出息,她过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答案可能是,她仍旧天天在小区垃圾桶附近捡破烂卖钱,甚至为了捡纸皮和别的大妈打起来。
纸皮大战,是北京老宣武区某老旧小区经常上演的一幕。小区每个垃圾桶,基本都被老阿姨们划片承包了。不守规矩的若来淘金,难免打一场。
对这些阿姨,土生土长的80后北京大妞菁菁“太了解了”。她爸妈均生在北京,有多套房子。菁菁硕士毕业后几经跳槽,找到心仪工作,年收入大几十万。她追求生活品质,吃穿用度都喜欢用不带大logo的低调小众奢侈品。她妈妈则完全不同,“一花钱就有罪恶感”。
周日早上,睡到自然醒的菁菁打车到三里屯,和发小薇薇相约在咖啡馆,吃brunch,人均一百多块。薇薇硕士留学归来,在喜欢的公司上班,同样生活优渥。菁菁点了杯七八十块的单品咖啡,呷了一口,努力去捕捉其中桃子的香气。“我妈要是看到咱俩花这么多钱喝杯咖啡,肯定会说咱俩造孽。”菁菁对薇薇说。

“为什么你妈条件这么好,却虐待自己?”
菁菁首先吐槽。不久前的雾霾天,年近七十的妈妈要穿越京城办事,嫌地铁贵,执意搭公交,单程倒来倒去两个半小时。菁菁的网约车账户余额不少,不忍妈妈折腾,就拿起手机要叫车。与往常一样,老人死活不同意。拿老年证可以免费坐车,在公交车抢上抢下和占座方面,她已很有经验。
“我妈也这样,她的信条是:能苦着自己的,就绝不花钱享受服务。”薇薇说。她妈妈也绝不打车,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夏日炎炎。一个三伏天,薇薇从地铁站打车和爸妈回家,花了17块,妈妈唠叨一路,“这个钱花得太冤了”。
薇薇请小时工做家务,妈妈像防贼一样在旁边看着。无论小时工多么卖力,在老人眼里都是偷懒,“这钱花得不值!还不如给我,我给你干呢”。至于洗碗机、吸尘器、厨余粉碎机等年轻人深爱的家居用品,薇薇妈一律不接受。她坚持能自己干的事情,就不要花钱用机器或者请人。
家里的车,多半像是摆设。因为一上车老人就觉得心慌,一加油就焦虑,总觉得自己坐车去办的这点事,“不值这个油钱”。
除了不开车不打车,还不能出去吃饭,一出去吃就闹别扭。妈妈的目光总集中在价格而不是食物味道上,对一道菜的唯一评价标准是“值不值”,口头禅是“我可不吃”。刚点了两个菜,薇薇妈就急赤白脸了,“不要了,不要了,点那么多吃不了”。薇薇很郁闷,即便那些自己觉得好吃,点评都是五星的餐馆,妈妈吃后也总是一脸怨气:“不好吃!瞎花钱!”看到别的餐桌剩饭很多,有的几乎没动过,老人难以克制冲动。要不是薇薇拦着,她不介意把四周桌上没怎么动过的菜都打包带走。

薇薇周末和老公回娘家,妈妈常常端上吃了好几天、已经反复加热的剩菜。有一次,薇薇发现两周前打包的食物,虽然已经面目全非,妈妈又给端上桌了。妈妈自己做的话,通常是一碗炸得齁咸的酱,一家人煮一锅面条就着吃。
虽然都有高血压,但咸菜依旧是薇薇妈和菁菁妈的挚爱。隔三差五,她们就会花几块钱买个大芥菜疙瘩,放酱油和盐炒一大盆咸菜丝,自己留一罐子,其他的装进罐子,和街坊四邻的老姐妹们分享。这些老阿姨们,也多是因早年拆迁分房,人人家里好几套,独生子女住一套,租几套,再加上退休金,说财务自由也绝对不为过。
薇薇妈还舍不得扔长了霉斑的面包和馒头,把发霉的部分抠了,接着吃。薇薇纳闷,“天天转发食物相克的养生文章,怎么真的跟她讲科学,就是不听呢”。她反复劝阻:“没发霉的也布满菌丝了,可能中毒!致癌!”妈妈就回一句:“不能浪费粮食!”粥馊了,什么东西长毛了,老人还有一个理论:“吃了这些,破破肚,拉拉稀,正好去火减肥了。”有一次,薇薇把长了霉点的面包整个扔了,妈妈又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偷偷摸摸吃。
菁菁和薇薇的父母家,虽然房子面积不小,但共同的特点是“乱”,囤货无数。冰箱里存的“僵尸肉”,能从年头吃到年尾。两位妈妈都没有收纳的概念和习惯,更别提什么“断舍离”了。同一功能的物品会有十几样到上百样,每一样的质量都不高,用薇薇妈的话讲:“断不了!舍不了!”她们最不能接受孩子花钱买礼物,分明是好东西,却百般挑剔,索要来发票,一边感慨“太不值了”,一边琢磨着怎么去退货。
两位老人背景非常相似:她们的父母1949年后从外地来京当工人,她们出生后不久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上小学不久又赶上“文革”。七十年代初,因政策改变突然有机会读了一两年高中,又突然因政策变化而终止,改去插队。几年后返城,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工厂或国营单位。恢复高考时,很多人已经工作,指着每月二三十元工资帮补家用,也就断了读大学的念想。

与儿女这一代不同,“单位”曾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提供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一辈子通常只干一种工作,生活中少有选择,尽管后来很多人下岗,但她们还是喜欢“铁饭碗”。薇薇妈总希望女儿能够进机关或国企——这些才算“正经单位”,或至少照这标准找个老公,但薇薇自有打算。这成为母女间日常争执的重要话题之一。
争执之二是,要不要每次住酒店都把一次性卫浴用品拿回家。从酒店拿回来的各种小梳子,家里快有半百把,酒店拖鞋一大摞。早市上几块钱一大包的那种叉子勺子,家里也有上百个,“没一个看得上眼的”。
菁菁家的争吵点则在于,要不要每次去超市都多揪一大把塑料袋回来。有一次,她回家看到满桌子满地拧成球的塑料袋,就知道是妈妈去超市水果区顺手囤的,气不打一处来,跟老人吵了一架。
薇薇老公从贫穷农村考入大学,后来留在大城市发展,给父母在县城买了房子,生活显著改善。“要说抠门,按理说应该是我妈,怎么也不应该是你妈。”老公在吃岳母做的发芽土豆轻微食物中毒后吐槽说,“为什么我妈现在可以享受生活,你妈条件这么好,却虐待自己?”
“你管我呢,我愿意!”
菁菁又好笑又佩服的是,在今天的北京,妈妈居然总能淘到个位数价钱的衣服。比如两块一条的“棉绒”秋裤,十块钱三条的“羊绒”围脖,一块钱一双的“纯棉”袜子等等。
“我周末一顿早饭钱,够她买一百多条秋裤了。”菁菁告诉薇薇,“你有空来我们家看看,简直就是袜子王国。哪哪都是袜子,厨房抽屉里,厕所纸篓里,枕头旁,沙发缝隙里。”她粗略统计过,妈妈的袜子有二百多双,攒成球藏匿在家中各个角落。
据老人说,这些“质量特别好”的“纯棉”袜子,几乎都是她从京城各个早市淘来的。即便如此,这位“袜子女王”还是经常补袜子。菁菁曾看到妈妈的一双袜子在脚后跟和脚趾处打了三处补丁。一起吃饭,经常可以看到妈妈从包中掏出一只袜子放在桌上,吃几口,袜子就亮了起来,她从里面掏出一个手机!原来,那是她的手机套。
薇薇妈则痴迷于囤杯盘。她家住城北,从街坊姐妹处获得重要情报:西南五环外某早市,有一块钱一个的碗卖,“出口级的瓷!”老人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次日早早起来,乘坐公交车穿越京城,往返近100公里,买回一打盘子和几个杯子。薇薇看到盘子上那些胡乱拼凑不知所云的英文单词、那粗糙的印花,“打碎这些破烂的心都有”。

更令她崩溃的是,没过几天,妈妈又从另一个老阿姨处得知,密云某大集有更便宜的碗卖!老人再次兴奋了。不过这次往返要快200公里了,这位阿姨还不忘嘱咐:“你稍微等等,拿了老年证(可免费乘坐公交)再去。”
薇薇妈退休前在事业单位上班,退休金不低,但是她始终无法享受逛大商场的乐趣,“看见价格三位数以上的衣服,就浑身难受”。她最喜欢去京郊顺义、大兴等地的各种大集,在里面逛着很有感觉。
对这些阿姨来说,任何支撑基本生存之外的消费,似乎都是奢侈的,所花的钱都是冤枉的。菁菁妈的很多同学朋友,日子也都越过越省。偶尔出去旅游,会提前买好几大袋子馒头烧饼,就着咸菜吃一路,避免下馆子花钱。
时至今日,仍有阿姨在家把水龙头开到不走表的最大滴漏程度,耐心等待滴水汇满水盆。菁菁妈有个同学,北京好几套房,孩子收入也高,但就是放不下存水的习惯。她家总是湿漉漉的,厕所根本下不去脚,满地是储水盆。脚底下是盆,台面上也是盆,不论洗什么,都不能用活水,全要用盆接着,再利用。洗衣机的水也不能浪费一滴,全都接出来冲厕所。
每次周末回妈妈家,菁菁都要先对自己反复做心理建设:这是她的生活,她高兴就好。但一见面,看到因反复加热而变色的饭菜,一屋子捡回来的破烂,这辈子都穿不过来的袜子,她就心烦。
“你为什么总是抱着匮乏不撒手?”
“你管我呢,我愿意!”
争执后,菁菁背着妈妈,扔了两抽屉袜子、一袋子梳子、一筐雨伞和好几大包勺子。“但是我发现,扔了之后东西仍不见少。”
“有一双无形的手把我按住。”
面对一直难以理解的妈妈,菁菁后来干脆就懒得理解,甚至回避接触。
直到有一天,她去看望妈妈的同学淑珍,绕不开,又谈起妈妈日益疯狂的省钱行为。“现在偏执得要命,春节恨不得也是顿顿剩饭,简直不可理喻。”
阿姨淑珍则劝她多理解妈妈。她给菁菁讲了一些她从来没听过的往事。虽然很多人因为拆迁或买房早,家中有几套住房,童年其实并不富裕,和一大家人蜗居大杂院,过的都是苦日子。他们小学同学不久前组织聚会。半个多世纪不见,大家还能记得当初谁家有高级奢侈品——沙发,谁家是干部家庭,衣服上竟然一块补丁都没有。
淑珍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常常挨饿。在供销社工作的亲戚把被耗子啃过,还沾着老鼠屎的碎糕点拿回家喂鸡,她曾耐不住饥饿偷吃那些鸡仔的糕点。黑棉鞋穿得发白,没钱买新鞋,她就在烧火的炉子下蹭黑灰,把棉鞋蹭得黝黑,跟新的一样。第二天上体育课,被烤糊了的鞋一下子绽开白棉花出来。她还在班里带头把铅笔写过的作业本用橡皮擦干净,擦出一个新本子来。老师表扬她“艰苦朴素”。

“我小时候,有一天数衣服上的补丁。上衣22块,裤子17块。”淑珍告诉菁菁,“我家还是双职工。你妈家就你姥爷上班,养活七口人,条件更差。你妈又是老大,还得操心弟弟妹妹。”
“那时候垃圾都要抢。”每天下午五六点,会有垃圾车集中倾倒。小朋友主要去捡烂纸和废品,还有外面是灰白色的、没烧透的煤核。拿小棍把外面的敲了,只要里边黑的部分。有一首民谣形容当时捡破烂的小孩:“身披盔甲,手持钢叉,脚踩风火轮儿,走起路来嚓嚓嚓。”淑珍解释,盔甲指的是哥哥姐姐传下来的补丁满身又不合身的衣服,钢叉是勾废品的钩子,风火轮是用废轴承和木板自制的单脚滑板车,嚓嚓嚓是轴承和地面摩擦发生的声响。
淑珍说,他们这代人普遍经历过对匮乏的恐惧,买东西不会想着喜不喜欢或者好不好,本能反应是“值不值”。无论买什么,心里首先会出现一个估价,高过这个估价的,看都不用看。她特别理解很多同龄人仍痴迷于捡纸皮和废品回收,“我们从小就懂废物利用。现在看到什么,仍会条件反射地想这东西还能怎么用。就怕浪费,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经历过的匮乏,你们难以想象。你们老让我们潇洒,我们敢吗?每当我想要花钱的时候,都有一双无形的手把我按住。”淑珍说着说着哽咽了。
想着淑珍阿姨的话,菁菁回家后第一次心平气和地问:“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袜子?”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袜子,我觉得穿袜子太奢侈了。”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菁菁妈说,每次因为袜子吵架,事后她也反省,可一看见袜子还是忍不住想买。她小时候穿不起袜子,好不容易得到一双塑料凉鞋,还常常开裂。十岁的菁菁妈,已经学会用烧红的火筷子补鞋。她的童年梦想,就是能穿着袜子配凉鞋。
每当妈妈稍微流露出一丝脆弱的时候,菁菁都觉得妈妈很陌生,她只在这种时候涌起很强的冲动想去拥抱她,却又只是坐着不动。
“你老让妈妈潇洒,又旅游,又泡脚按摩,又享受生活,我觉得钱可不能这么花。没有囤积,生活就没有保障。”她还向菁菁传递从小听到的教导:“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已经内化成她的人生信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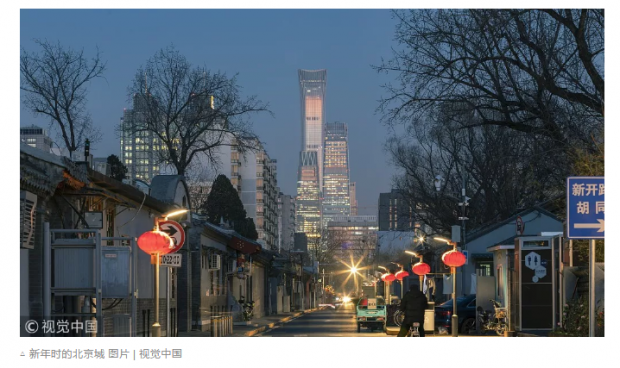
菁菁妈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最爱谈论的话题就是“你退休金多少”和“开什么药”。养老成为他们的心结。他们普遍伺候过卧床的老人,家里好几个弟兄姐妹尚且周转不过来,也领教了请保姆的难。菁菁妈说,大家现在省钱,很多是为了应付自费医疗项目,为了在不远的明天给自己找个好的养老院,卧床了能请得起保姆。“咱下一辈都是独生子女,能指得上他们给咱擦屎端尿?”
听到这些,菁菁反复强调:“我怎么会不管你?有我呢,你放心吧。”
“我不给你添麻烦!再说了,我指得上你吗?”依旧是那种熟悉的强势语气。稍微和缓下来的菁菁,不由地再次心生反感。
不过爸爸告诉她,每次女儿回家前,妈妈都很紧张,“你妈其实特别怕你批评她,但又达不到你的要求,就只能跟你杠”。
菁菁还没有想好,和妈妈长久以来的“爱恨交织”的状态,如何才能结束?
她决定,妈妈今年过生日,一定带她去大商场,让她选最喜欢的鞋和袜子。
但她转念一想,妈妈肯定是不会去的。
本文2019年3月15日首发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guyulab),经授权转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